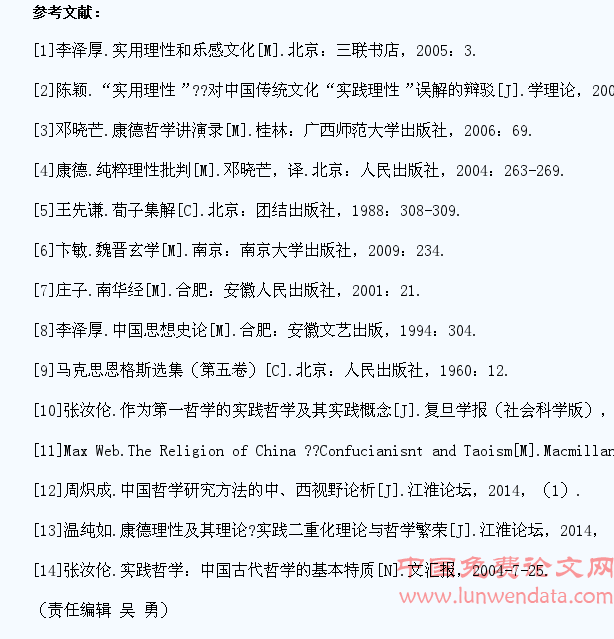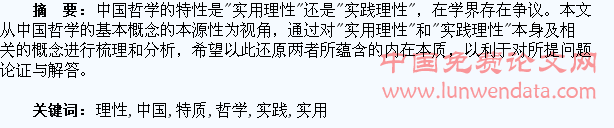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132-004
学界常见觉得中国哲学是以“实用理性”为其存在形态的,或者“实践理性”与“实用理性”在指中国哲学时并不完全加以区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李泽厚先生在其历史本体论中所表明的看法。李泽厚觉得,“实用理性”乃是经验合理性的概括和提高,人类的经验源自实践。实践是用-制造工具的劳动操作活动,人类在生产劳动中不但产生了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社会语言、文字、艺术,还形成了系统的有关的理论体系。[1]李泽厚声称,他的“实用”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是在价值层面而非纯理性层面。马克思主义觉得,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认识不但从实践中产生,并且为生产实践服务,而认识的正确与否,还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可见,李泽厚的“实用理性”和马克思的实践论,无论是认识的来源,还是认识的目的几乎都是吻合的,所谓的“理性”,不过是感性经验的思维抽象,即人类对感性的认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和马克思的实践论是相一致的。不过,马克思实践论更多强调的是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而中国古典哲学虽然也不反对人类的理性认识来自“格物致知”,但它更重视的是人的精神上的修养和人格理想的塑造。可见,“实用”和“实践”在这里并不可以划等号。因此,李先生称中国哲学为“实用理性”有它的实质问题。还有一部分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传承的角度,通过“实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比剖析,觉得“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自己性格具备的特点,反对理论界用康德的“实践理性”对中国哲学作解释,觉得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一种误读”[2]。这种说法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为参照,并与“实用”相等同,但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实践”相不同。后者是正确的,正如邓晓芒先生剖析的那样,康德的实践理性“跟感性世界没关系,涉及物自体的问题,是人的自由、人的实践能力、人的意志、人的欲望等问题。人本身不是从认识出发,无需积累很多的经验,然后才有意志,才有欲望,而是刚开始就有些”[3]。也就是说,人的实践认识是先天就拥有的,而不是后天从感性或经验中获得。这一点与柏拉图的绝对的“理念”和中国宋明时期理学家的“理”的范畴倒有几分相似。那样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具备“实践理性”?本文试以中国哲学基本定义的本源性为视角,通过“实用理性”和“实践理性”本身及有关的定义及范畴的梳理和剖析,并从历史的角度解析其内涵价值层面的意义,借用史与思、理与逻辑的结合,还原两者所蕴含的内在本质,以期对此问题有个客观实在的解答。
1、理论与理性
就根本含义而言,“理”,指的是客观事物自己运作的次序、事物或事件存在的根本规律;“论”则有剖析判断之义。理论就是社会实质日常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实践有系统的认识通过思维的综合上升而形成的认知结果,它是以形而上的方法存在的。因此,李泽厚先生所说“理性”其实就是“理论”,由于他给“实用理性”所作的讲解就是大家对现实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一种有系统的概括。但这种“实用理性”和大家所说的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具备本质不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理性的剖析有两种基本的讲解,第一,他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或者称为纯粹理性和一般理性[4]:理论理性不是通过实践的深思而成,亦非推理而得出,在康德看来,它实质是人先天拥有的,类似部分儒家学者对心的本然之性的认识,“心生而有知”,“凡以知,人之性也”[5]。“知”是心本然的一种认知能力。可见,康德的理性并不等于理论。不过,理性和理论不可截然分开。没理性的存在,理论是没办法形成的,没理论,理性自己存在的开显也成了问题。第二,假如说李泽厚的理性具备实用主义色彩的话,那样康德的理性却隐含着对人类常识进步的一种导向,引导着大家对常识的无限诉求,同时内藏着对生活将来的一种向往,因而精神价值上的意义是凸显的。这也正是康德的实践理性理论出现是什么原因所在,它回答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哲学方面所提出三个问题之第二个问题所涉及的:“我应该干什么?”即人类的实践。因为它源于个体本性的自觉,无需外在强制力的驱使或约束,这种理性的内容应该是先天的,行动出于个体的自愿,因此它应该是道德的实践。也就是说,康德的实践理性不过是人的先天意志在社会日常的实质应用而已,人的本性意志即是实践理性。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所说的理性和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理性的意思是有巨大差别的。李泽厚的“实用理性”本质是把生产生活高度系统抽象的结果,就是一种实用理论,是在社会经验中后天获得的。康德所说的理性则是人的一种能力或者本然意志,二者并没根本上的一同之处。不过,康德的实践理性虽然超越了社会生活实践,但并没脱离它们,它所反映的恰是大家在现实日常因为种种缘由暂时还没办法达成的社会理想或目的的理论首要条件。从中国古时候哲学来看,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亦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把人天生的自然本性作为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与对社会生活的美好向往。譬如儒家“以仁爱性善作为做人的规范,其理想人格是圣贤,所追求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6]。道家则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倡导效法天道,顺物性而为,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7]的理想。如此,儒道的“仁爱性善”、“自然本性”与康德的实践理性在理论来源与功能和用途上无疑有着较多的一致性。从哲学的根本任务来讲,哲学是对人的生命意义大体上的思索和追问,而不具体涉及大家日常的思想行为。因此,把哲学与“实用”理论联系起来并不完全妥当。
李泽厚的实用理性即实用理论,或者说,理性等同理论,但康德的理性表示的则是一种意志或能力,当它和实践联系在一块时,其表示的价值内涵与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论表现出同一思维理路。从哲学的角度看,实用理性与实践理性相比较,后者更能全方位地反映中国哲学的特质。当然,它所体现的内容和实质与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有什么区别也是明显的,这是需要认识到的。 2、实用与实践
“实用理性”中的“实用”一词,第一从字面上来理解,无非是说中国哲学的理性重具体的价值层面有哪些用途或功能,轻理论的思辨。正如李泽厚所说:“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的思辨的道路,也没走向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8]第二,“实用”也明显遭到西方“实用主义”派别思想的影响。“实用主义”的原意就是行为或行动,它在哲学上强调立足现实生活,重视行动本身,所有理性都要用实践去引导、规范,甚至用来塑造人的情感和欲望。因此,“实用主义”又称“行动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这和“实用理性”中的实用原则是不谋而合的。最后,“实用”理论与中国小农社会的实质生产生活情况是符合的,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下,大家更关心的是其行动的现实价值。因此,恩格斯说:“在所有实质事务中……中国人远胜东方其他民族。”[9]事实上,中国哲学理论的产生并不来自下层劳动人民,而是来自贵族、士、儒,哲学和现实的生产生活并不具备直接的关系,并且,他们之间也没有完全重合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取向。以“实用”和“实践”为例:实践的平时意义和哲学意义并不相同,大家总是把所有人类的行为活动都看作实践。事实上的“实用”包含了生产生活及平时行为等行动,生产劳动等仅仅在于满足人的生理上的存活和欲望。但哲学意义上的实践不同于生产劳动,它涉及更多的是生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的自己就是目的,实践不是保持生命的生物活动和生产活动,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广义的伦理行动和政治行动。[10]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讲解和国内古时候对伦理道德的态度一致,践履、践行指向伦理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实行,无人会把赚钱、做工与实践或者践履联系在一块。[10]
虽然实践和生产活动在哲学意义上有着根本有什么区别,但它们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它们都需要人类作为主体去实行。在平时生活的语言中,大家不会在乎去区别哲学中的实践活动和日常实践的意思,一般指的都是第二个含义。不过在关系到一些基本问题的时候,作为哲学的实践与社会平时中实践有什么区别显然就会有它的根本性的意义。哲学中的实践是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行动,而日常的实践则是由社会具体环境决定的,人是受当下自然、社会的规律支配的;哲学上的实践重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生产的实践却只不过关心生理上的需要和满足;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对象是大家人类自己,而生产意义上实践的对象主要偏重物质。把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和生产意义上的实践假如混同,无疑是对哲学中实践上的人的意义和价值的消弭,哲学存在的基本意义或者说哲学的真的对象和任务就会引起大家的质疑和猜测。
不但在平时生产日常“实用”和“实践”的意思和界限含混不清,即便是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含义的理解也出现了类似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不但指的是人对自然物质能动的生产活动,而且还反映人际之间的行动,它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考虑他者的存在,这里就涉及人的行动和自由的关系,因此实践不再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生产活动之类的具体行动,而是在更高意义上人的思想上的应用。
通过对“实用”和“实践”的剖析和对比,哲学意义上的“实用”和“实践”有着不一样的含义和价值指向,用“实用”的定义实质是体现不了哲学的基本任务和精神的,因此,把中国哲学的特质归结为“实用”不但根本反映不了中国文化思想进步的轨迹,而且用“实用”也很难明确地梳理出中国文明演进的精神脉络。
3、超验与经验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中说:“中国哲学本身没一种沉思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中国哲学没一种理性的形式主义特征,不像西方的法理学那样。……中国哲学没产生经院哲学,由于它在职业上就不专注于逻辑,逻辑定义本身对中国哲学来讲是绝对陌生的。中国哲学只关注经文的书写,它不是辩证的,而是维持着对纯实践问题和世袭官僚身份利益的倾向。”[11]以韦伯的理解,中国的哲学就是一种经验性的,缺少超经验的理性的思辨和理论的形而上学。由此,包含他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断言,中国的哲学还不是真的意义上的哲学,或者更有甚者说中国基本没哲学。假如以形而上的角度看,中国哲学从先秦道家的“道”、“一”至魏晋玄学的“无”、“有”,一直到宋明理学的“理”、“欲”,以西方哲学的理性讲解方法,无不充满了决定精神和理念的特征。这类定义的提出,无论其背景或根源怎么样,仅从其表现形式来看,体现了人类思维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而非常难找到它们在现实世界相应的实体,就像西方上帝的定义一样。[12]假如从系统性和思辨性的视域来看,中国哲学在“天人合一”的大的系统下,有无之辩、名实之辩、性理之辩与天人之辩、理欲之辩、义利之辩等,充分说明了中国哲学对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深沉的、系统化的考虑,它们所彰显的进步维度和内在张力是中国哲学的厚重所在。假如以经验和超经验之分来判断中国哲学的特质(即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仅从儒家的一些主要定义来看就能回话西方哲学对理性的讲解方法。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其定义并不缺少在超验范围丰富的思辨玄想,也不缺少超越世俗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诉求。如儒家的“大同”理念、关于“圣人”的人格理想等。显然,这类思想具备理想性、超验性,而并不是韦伯说的只有“纯实践”。正是用这类超验思想指导客观的、实质的世俗生活,才使得中国人民在面对任何苦难和困境时,都能维持高尚的人格和不屈不挠的积极进取精神,而这类品质绝不是能以“实用”或经验得来。
在特定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具备肯定的合乎客观社会生活的理性,特别在道德理念方面,一度成为古时候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威,这权威在非常大程度上并不来自政治的干涉或者强迫。在近期的几十年间,儒家一些适当的道德理性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特别是在经济高速运行的环境下,反而出现了高调的回归。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中的道德理性具备现实性和合理性,也是大家把中国哲学看作实用哲学是什么原因所在。但其次,这种实用性却没办法掩盖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具备超验的、理性化的、常见性的理念、信念、观念等存在的事实。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特质就总体而言,用“实用理性”来概括无疑是不适合的。当然,这里无意说中国哲学的“实践理性”等同于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13]且不论康德对理性的划分是不是合理,仅就用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作为衡量中国哲学的“实践理性”的规范也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对的。无论内容的来源、构成的形式还是价值的规范、评价的原则,二者都是有非常大差异的。这好像还可以继续讨论。
总的来讲,以“实践理性”代替“实用理性”更能准确把握中国哲学的特点,揭示和体现中国哲学真的的蕴含,更为符合哲学的常见共性和根本性质。“其实,实践哲学并非什么新的东西,中国古时候哲学就能说就是一种实践哲学。”[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