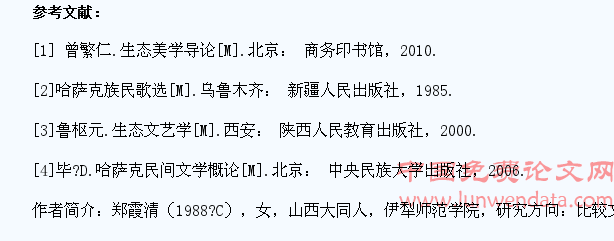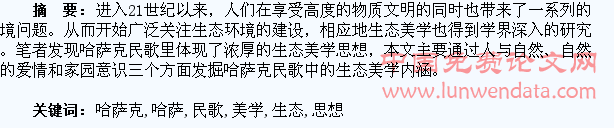
伴随社会的飞速发展,大家的物质水平得到明显提升,随之而来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一方面,人类所存活的自然环境遭到紧急破坏。譬如全球气候日益变暖,自然资源匮乏,空气污染、水污染紧急,物种的多样性渐渐降低,水土流失紧急等等,这类全球性生态危机正紧急威胁着大家所存活的环境和人类自己的健康。除去自然家园遭到破坏,人类的精神家园也在不断遭到挑战。全球化年代的到来使大家的思想观念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人的欲望像填不满的沟壑,过度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了精神范围的提升。个体崇尚享乐主义、资金至上、念书无用论等错误思想,人类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正在渐渐被忽视甚至颠覆。大家身上应该拥有些正确的道德观、个人品质、信仰、尊严正在慢慢变质。大家的精神陷入迷茫,人类的精神家园正在面临着危机。在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下也同时历程着精神世界的匮乏。在这个年代背景下,生态问题遭到了大家广泛的关注。那样与之有关的生态美学也就成了研究的热门。
对生态美学的概念,现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看法。狭义的生态美学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处于一种审美的生态关系,广义的生态美学则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与人与人自己的关系都处于审美的生态系统中。笔者更倾向于曾繁仁教授的看法,他觉得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与人与自己等多重审美关系,最后落脚到改变人类当下的非美的存在状况,打造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的存在状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况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1]哈萨克族民歌中蕴涵了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本文主要侧重于从以下三个方面剖析哈萨克民歌中的生态美,分别是对和谐的生态图景的眷恋之情、对自然化爱情的执着之情和对诗意家园的追慕之情。
1、对和谐的生态图景的眷恋之情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生态美学的核心范畴。哈萨克民歌里人与自然不分彼此,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块。哈萨克族人民生活在广大的中亚国内上,这里的生态环境十分优美。有高大葱郁的杉树、鲜花遍野的草地、巍峨雄壮的雪山、潺潺流淌的河流等等,这类没经过现代人污染的自然风景具备浓郁的生态美学特点。哈萨克族人民生活在大草原中,整天面对的是大自然中的蓝天、白云、青草、飞鸟,与它们进行对话,它们成了牧民最亲密的伙伴。因此,他们常常把大自然作为审美对象融入到日常。《兀立的白隼》《仙鹤》《云雀》《春季》《珍珠湖》等用朴实的语言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自然物的喜欢之情。比如《我心爱的菜鸟马》中满含深情地赞美我们的菜鸟马:“菜鸟马呀,我的良种马,赛场上你看上去那样优雅;你的额鬃比丝绸还好看,你的身材优美毛色光滑。”因为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从而自然地形成了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当然,它们不止是作为一种审美客体,更具备哈萨克族人民不能离开的实用功能。譬如仅仅拿自然界中的动物来讲,动物的皮毛为牧民提供衣服,肉和奶可以为牧民解决吃食问题,迁徙时候还可以长途跋涉为牧民驼运东西,充当交通工具。而自然界中的其他事物,譬如河流、森林、土地等都是哈萨克人民存活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因此,这类自然物成为哈萨克民歌里大力歌颂的对象,得到大家的珍惜和爱惜。在民歌中随处可以感觉到大家和自然融为一体,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具备独特的哈萨克草原文化气息。譬如在《在牧场上唱歌》中短短的十二句话里涉及到了草原上哈萨克族人民平时生活的情景,高高的白杨树、远处的毡房、戴圆帽的女孩、扬鞭上山冈、赛马叼羊、小溪、汲水的女孩、牧场、篝火、对唱的女孩等,大家在大自然中安宁地生活,人与自然构建了好、平衡的生态关系,构成了一幅淳朴和谐的草原生态图。
2、对自然化爱情的执着之情
社会生态是人与周围环境所形成的生态系统。爱情是人与别人之间产生的关系,因此笔者把爱情归为生态美学中社会生态的范畴。哈萨克民歌里的爱情占据着很大的比率。而哈萨克情歌里的心上人大都用自然界中的景物来作为比喻的对象。这类单从标题上就能看出来,譬如《我的花朵》《你象月亮》《天鹅落在草滩上》《红珍珠》《心中的玫瑰》《你的双眼象秋水》等。这与他们所生活的哈萨克大草原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从小到大在自然中成长,在自然中积淀,在自然中感受。潜移默化中大自然成为他们表达情感最常见的对象。这种融入自然的爱情本身就是对好的生态环境的观照,不只体现了热爱自然的生态意识,同时体现了大家中对生态性爱情的憧憬和赞美。
哈萨克民歌中的大自然不只用来比喻客观具象的人,还是创作者生活理念的形象载体,通过寄情山水、花草鸟兽来传达作者的精神诉求。借用自然表达作者面对爱情时忐忑、焦虑、不安或是甜蜜、开心等情感,以达成内心的平和安定。他主观上觉得周围的自然景物都是有情感和思想的,都会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这可以看出作者本能上把大自然当做自己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向它们吐露衷肠。体现了对自然依靠、信赖的生态意识。当爱情遭遇挫折时,周围的景色仿佛也变得晦暗无光。《绝情的叶尔特斯河》里创作者没办法了解他们的心意,心情很焦急忐忑的状况下,看到叶尔特斯河也是绝情的、“恶浪翻滚”的。《浅栗色的母鹿》里作者与母鹿同病相怜,母鹿的身体让人击伤就像“我”的心被爱情击伤,通过母鹿的不幸遭遇暗示了我们的悲伤。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爱情与自然融为一体。
自然化的爱情指的不止是与实体的自然融为一体的爱情,也指爱情本身具备大自然般淳朴、自由、纯粹、天然的特质。哈萨克民歌里的爱情是简单而美好的。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地位、资金、权力等世俗利益的羁绊,是社会生态中一种审美存在状况的体现。哈萨克民歌里爱情的自然化,第一体目前他们遵从我们的内心,喜欢就大胆向他们告白,不受其他世俗原因的影响。譬如《阿依黛》《我的花朵》《漂亮的女孩》等不少情歌都很直率地袒露自己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有着率性、天然的爱情观,是原始生命力的张扬。反观现代社会的爱情,参杂了太多世俗的东西,哈萨克民歌里宣扬的那种纯粹、朴素的爱情愈加少。这种纯真、简单的感情对现代人具备肯定的启示用途。第二,哈萨克民歌里的男女在面对爱情上有着执着的信念和决心。虽然面临重重妨碍,仍旧不考虑所有,坚持不懈。哈萨克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需要通过不断地迁徙来探寻水草丰美的牧场。面对迁徙等缘由导致的离别,情大家只能借用于歌声来排解我们的相思之苦。然而歌声里传达的并非抱着悲观、舍弃的心态,而是表明了不管现实多么无奈,也肯定坚守初心,对爱情不离不弃。《我不过分忧伤》里唱到“不管她远走天涯海角,早晚总会回到我的身旁。”作者怀着乐观的心态耐心等待和爱人成为眷属的那一天。《心愿》里即便情人已经不知去向,作者还是坚守着我们的爱情,吐露了“我还在等着你,一往情深”的心声。同样的主题还有《莫做负心人》《巴哈迪霞》《小花马》《我们两个》等等。比起现代人追求物质、讲究速度的爱情观,哈萨克情歌里传达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爱情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力量。他们的爱情朴素而简单,遵从了人类的生态本性,是未经现代世俗观念浸染的原始驱动,是人类内心深处的真正召唤。这种爱情表达了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生态理想。 3、对诗意家园的追慕之情
家园意识是生态美学的要紧内容之一。家园意识最早是由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来的,他觉得家园就是“依寓”、“逗留”在熟知的世界中。他在《追忆》中提出了“诗意地栖居”这个著名的美学看法。他所表达的基本内涵就是人要审美地栖居于大地上,那样人与所居住的世界就要达到和谐平衡的理想状况。这样来看,家园意识指的不止是物质上对家乡的热爱和亲和,更在精神上给人以一种“在家”的感觉,使人的内心感到安宁、祥和,使人的灵魂找到栖居的地方,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哈萨克不少歌谣里都讴歌了自己漂亮富饶的家乡,并表达了对家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在《富饶的家乡》里创作者满怀深情地歌颂了我们的家乡。“隆起的山冈”、“无边的草原”、“牛羊撒欢”、“彩蝶嬉戏”、“山风轻轻地吹拂”、“牧草在微微摇曳”、牧民唱着悠扬的歌、牧羊女孩的彩裙在山巅翩翩起舞……所有都看上去那样美好,哈萨克族人民生活在如此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里,与世无争,无忧无虑。这种对家乡的歌颂还有《漂亮的伊犁》《草原的景色》《旷野》《富饶的阿勒泰》《三条河》等等。在哈萨克民歌中,他们愉悦地生活在这个美好的自然家园中,使生态系统达成平衡的进步。
哈萨克民歌里还有一部分是表达对家乡很难舍弃的依恋之情,譬如《出嫁时的告别歌》《出嫁歌》《离别歌》《哭嫁歌》等。在这类民歌里大多数是外嫁女出嫁前对家乡唱的歌,字句充满悲切和不舍。譬如在《出嫁歌(一)》里面,作者一连唱了十三句“再见了家乡,我祝你平安。”可见家乡在他们心中无可取代的地位。在这类将要离别家乡的人的眼里,这个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居住环境,而是上升到精神范围的故乡,它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个精神上的信仰之地,具备永恒的意义。因此在面对与故乡的离别时会产生无尽的乡愁。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总忘不了我们的故乡,那里凝结着他们温暖的的记忆。故乡的亲人、乡邻、伙伴,与土地、树木、花草、动物都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这是任何地方都不可取代的。那样家园的真正内涵是大家更接近于本源的地方,是情感得以依托的地方,是灵魂可以得到安宁的地方。反观现代人的存活环境,伴随技术对人类自己的“促逼”,不但自然家园遭到紧急污染,大家的精神家园也在慢慢缺失。因此,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要保护我们的家园,使大家的存活空间不遭到污染,致力构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和谐共存的理想家园。这个家园,不止是狭义的养育个体成长的小家园,更是一个保持生态系统好进步的广义上的宇宙家园。
综上所述,大家挖掘了哈萨克民歌里所蕴含的宝贵的生态审美价值,哈萨克民族这种存活方法体现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这对现代人达到审美的存活状况有肯定的借鉴用途,使大家对工业文明进行深思与超越,从而更好地构建大家的生态文明社会。